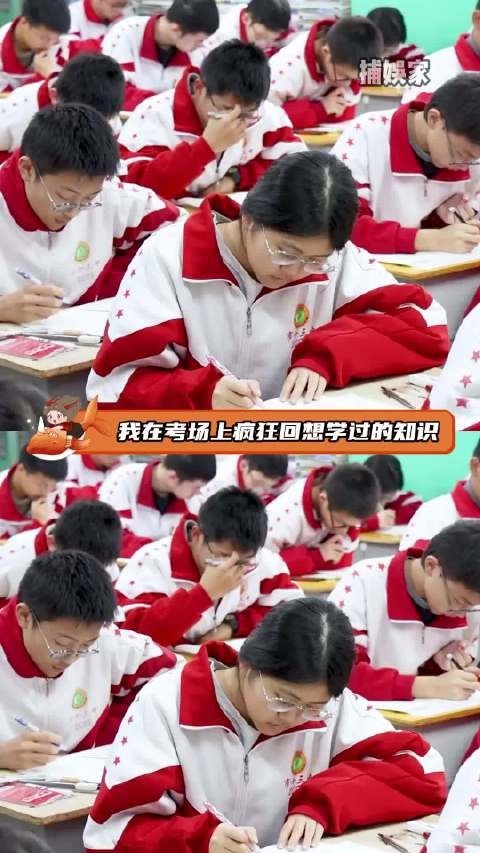水兵:碧霄一鹤乘风起——程韬光与他的大唐诗人传|中原作家
《唐诗三百首》辑录了唐代近300位诗人的作品,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华选本。 #生活常识# #历史文化普及#
作者:水兵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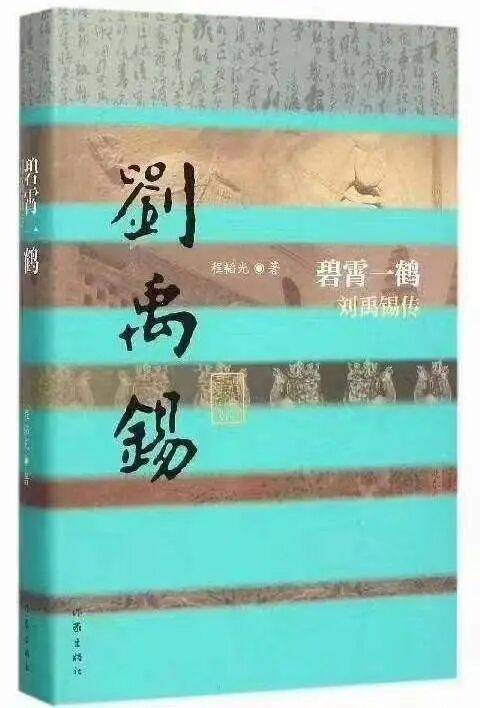
《碧霄一鹤——刘禹锡传》
一
一碗水放在那里不动,它自然就是平的——你非要端起来,那就需要端得四平八稳,小心翼翼,稍一疏忽,就会把水洒了,这就是平则稳,动则流的真理;要么你得有超人的魔力,无形之中,把控一切。
诗人、教授、长篇历史小说作家程韬光属于后者。
唐宋诗词,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巅峰。像范仲淹描写烟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湖一样“衔远山,吞长江,浩浩汤汤,横无际涯;朝晖夕阴,气象万千”。而为大唐诗人作传、评诗论诗的著作,自唐以降,更是汗牛充栋,不胜枚举。
时隔千年后的一个晚辈后生,在现代化科技化智能化的滚滚红尘中,却敢宵衣旰食,披沙拣金,以现代人之视野、眼光、胆识,穿越时空,以人性之光辉,心灵之相契,为他们作传,接连推出洋洋四部巨著,何也?
五月,天上像有十个太阳,照得大地一片金黄。这是收获的季节,也是劳动者狂欢的节日,我却颈椎腰椎病犯起,蜷在床上不能行走。
移床临窗,五月的阳光斜照着,我的颈椎与腰椎仿佛被钉入盛唐的青铜钉,每一次翻身都听见骨骼深处传来历史的回响。床头四卷本的大唐诗人传记,在光晕中展开金戈铁马的幻象——李白的剑气刺穿纱帘,杜甫的秋兴漫过窗棂,白居易的琵琶声入耳如风,刘禹锡的玄都观桃花灼灼如血。此刻,程韬光的文字化作一剂汤药,让困于方寸之躯的灵魂,得以乘鹤直上碧霄。
这位来自中原南部的邓州籍作家,用现代笔法为诗人们煮诗画像。当现代社会无数人沉溺于手机碎片化阅读时,他执拗地以长篇历史小说的形制,将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刘禹锡从岑寂的古代文学史中释放,让他们重新在纸上饮酒、行吟、痛哭、长啸。这不是简单的历史复写,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——作者手指划过,分明能听见盛唐的车马与当代的键盘在字里行间啪啪作响。
诗人一辈子一定要写上几首大诗,作家一辈子要有几篇有意思的作品,以上帝的视角,俯视大地、苍生和自己,思索历史、现状和未来。以真诚的心面对现实,文字中禁止作恶,哪怕平庸的恶,也不行!
评人评书,亦应如是。
韬光是我的老乡,古邓国人。古邓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诸侯国。“邓”发轫于“夸父追日”死后所化“邓林”之“邓”。它是楚的母舅国,外甥楚文王借道伐申,归来途中,顺手灭了舅国邓,重又上演了“假途灭虢”的故事,可见邓国的善良与大度。
邓国变为楚国领地,自有楚人飘逸的性格,浪漫而绮丽,韬光是“邓大国”的后人,自有楚风遗韵;北宋时有开国宰相赵普和其后的副宰范仲淹在这里知州,一派大家之情怀。
韬光早年写诗,是诗人,但他喜爱唐诗,崇拜仰慕唐朝的诗人,就选了唐朝不同时期四个有代表性的大诗人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刘禹锡,为他们作传,以此解读他的人生爱恋,就有了这四部:《太白醉剑》《诗圣杜甫》《长安居易》《碧霄一鹤——刘禹锡传》。作品一出,震撼了文坛,震撼了历史小说界,自此对唐朝诗人和诗歌又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探寻热潮。韬光也成了研究唐诗和唐朝诗人的专家,游走高校文坛、讲坛,讲课几百场,粉丝数百万,从而成为解读唐诗和大诗人成长过程的“新导游”,被喻为“让唐诗重新飞翔的人”。同时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路经,由郑州市文联、作协的一个工作人员转而成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授、校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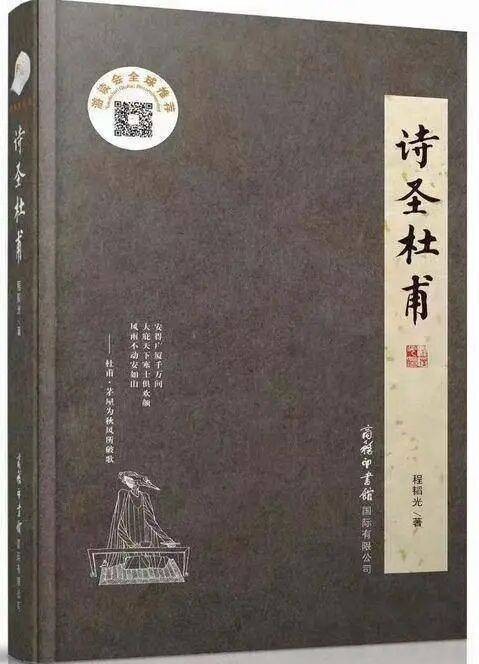
《诗圣杜甫》
二
长安城,总让人想起李白笔下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”的盛唐意象。在这个被历史浸透的意象里,程韬光像一匹从汉唐古道驰来的青铜马,携着中原腹地的楚风汉韵,叩响当代文坛的城门。这位以诗性笔触复活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、刘禹锡的作家,用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构建起一座精神灯塔——当现代人在钢筋森林里迷失时,这座灯塔正以唐诗的平仄为经纬,重新校准着文明的方向。
邓州古城墙下的黄土,沉淀着三千年的文明密码。当程韬光站在穰城遗址上,脚下是楚人“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”的创业史,远处是范仲淹知邓州时建下的花洲书院。这座被《诗经》浸润的土地,将两种文化基因注入他的血脉:楚人的浪漫绮丽与宋儒的忧患意识,在《太白醉剑》中化作剑气纵横的狂草,在《诗圣杜甫》里凝成沉郁顿挫的碑刻。在《碧霄一鹤》中,刘禹锡被贬朗州时的《竹枝词》创作,被程韬光演绎成一场人与自然的“通灵”仪式。刺史府衙的烛火与沅江渔火交相辉映,刺史与渔夫在月光下对饮,这种超越阶层等级的生命共情,正是屈子“哀民生之多艰”的时代回响。而当写到白居易《观刈麦》时,他又化身为新乐府运动的书记官,用小说家的显微镜观察唐代农人掌心的茧纹。
这种双重视域的融合,让他的历史小说呈现出独特的价值取向。在《长安居易》中,大雁塔的阴影不仅是佛教东传的见证,更折射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。程韬光如考古学家般剥离着历史的地层:表层是“慈恩塔下题名处”的进士风流,深层是“心忧炭贱愿天寒”的民生疾苦,而在更幽微处,藏着当代文人面对浮名与赤忱的永恒叩问。
在《太白醉剑》中,他解构了“诗仙”的神话面具。当李白在终南山炼丹炉前写下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时,程韬光注意到道童手中扇火的蒲扇已烧焦边缘——这个细节泄露了求仙问道背后的生存焦虑。而在《诗圣杜甫》里,“朱门酒肉臭”的名句诞生场景,被还原成一场暴雨中的视觉震撼:权贵宅邸倾倒的馊肉与贫民窟的泥浆混流,形成长安城地下特有的血色眼泪。
韬光拒绝平庸之恶,用文学良知锻打塑造着时代的青铜力量。
他常说,知识分子应该有知识分子的担当,我们虽不能做些惊天巨事,但“写诗者当如铸剑,淬火时可见肝胆”,这种创作伦理也贯穿其四部曲始终。他笔下的杜甫在“三吏”“三别”创作期,总会梦到那些死去的征夫和无奈的冤魂。这种将文学视为生死契约的严肃性,恰是当代文坛珍贵的品质。
诗人杜甫“朱门酒肉臭”是带着血的控诉。韬光编织塑造人物时时常设计出超现实意象,实则是文学良知的图腾——真正的诗人必须承受语言的结石之痛。虽然写古人是跨时空对话,但文学的良知是见证苦难时的不可承受之重。
三
邓州城外的湍河,流淌着三千年的文明基因。这里曾是《诗经》里“南有乔木”的吟咏之地,是楚人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的求索起点,是花洲书院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精神道场。程韬光的笔锋,天然携带着这方水土的符号密码:楚辞的巫风绮丽与宋儒的忧患意识,如同水墨画的浓淡相生,在其作品中碰撞出惊人的张力。
在《太白醉剑》开篇,他让李白在云梦泽畔遇见少年屈原的“幽灵”。两个楚地狂人隔空对饮,屈子的香草佩剑与李白的金樽清酒交相辉映,月光下楚辞的九歌节奏与新诗的散句自由完美共振。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,恰似邓州古城墙上斑驳的夯土层——楚人的浪漫血性与中原的浑厚气脉,在程韬光的叙事中熔铸成独特的文化特质。而当笔触转向杜甫,他又化身考古学家,用小说的洛阳铲深挖“诗圣”的士儒基因。《诗圣杜甫》中那个在秋风中紧护茅屋的身影,分明与范仲淹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”的剪影重叠。程韬光在此揭示了一个惊人发现:盛唐诗人的精神图谱里,早已埋藏着承接千载的忧国忧民情怀。
写作也同酿造好酒一样——以史实为原料,用诗性做酒曲,在时间的窖池中长久陈酿。他的四部曲没有廉价的历史戏说,也不做学术考据的奴隶,而是让想象力在史实的框架内纵情舞蹈,在限制中迸发惊人的艺术想象和自由。
此刻,床上的我突然顿悟:程韬光的四部曲,本质上是一场持续的精神突围。从《太白醉剑》的个性解放到《诗圣杜甫》的悲悯担当,从《长安居易》的世俗洞察到《碧霄一鹤》的超然豁达,恰似刘禹锡笔下那只穿越风暴的仙鹤,在历史的碧霄上划出一道亮丽的彩虹。我僵痛的脊椎此刻也仿佛长出鹤的羽翼——想飞。也让我顿悟:真正的飞翔,从来不是挣脱地心引力,而是学会在重力中起舞——当我们无法改变肉身的困境时,至少可以让精神乘着文字的翅膀,冲向九万里的碧霄天空。
韬光的文字,像黄河之水天上来,像大江东去浪花涌。韬光的长篇历史人物传记,也和书中的诗人一样,熠熠生辉,星光无垠。
[作者介绍:南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]
(本文原载于《中原文学》2025年8月刊)
网址:水兵:碧霄一鹤乘风起——程韬光与他的大唐诗人传|中原作家 https://www.ashwd.com/news/view/184033
相关内容
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的《宗师列传·大唐诗人传》这两张牌联手,简直就是王牌组合 王鹤棣秦霄贤 秦霄贤 王鹤棣
果然,与老友共乐最畅快无比王鹤棣范世琦欢笑满堂丁程鑫
贺知章,大唐最幸福的诗人
秦霄贤孟鹤堂扑面而来的电影气息…
张丽明:在杜甫草堂,与诗圣对视|中原作家
录制综艺节目遇见了丁程鑫和秦霄贤…
王昌龄堪称大唐直性子
台湾作家司马中原去世,生前曾说:两岸同文同种、“去中”没道理
【故乡里的名诗】大唐最深情的诗人!解锁李商隐诗歌浪漫密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