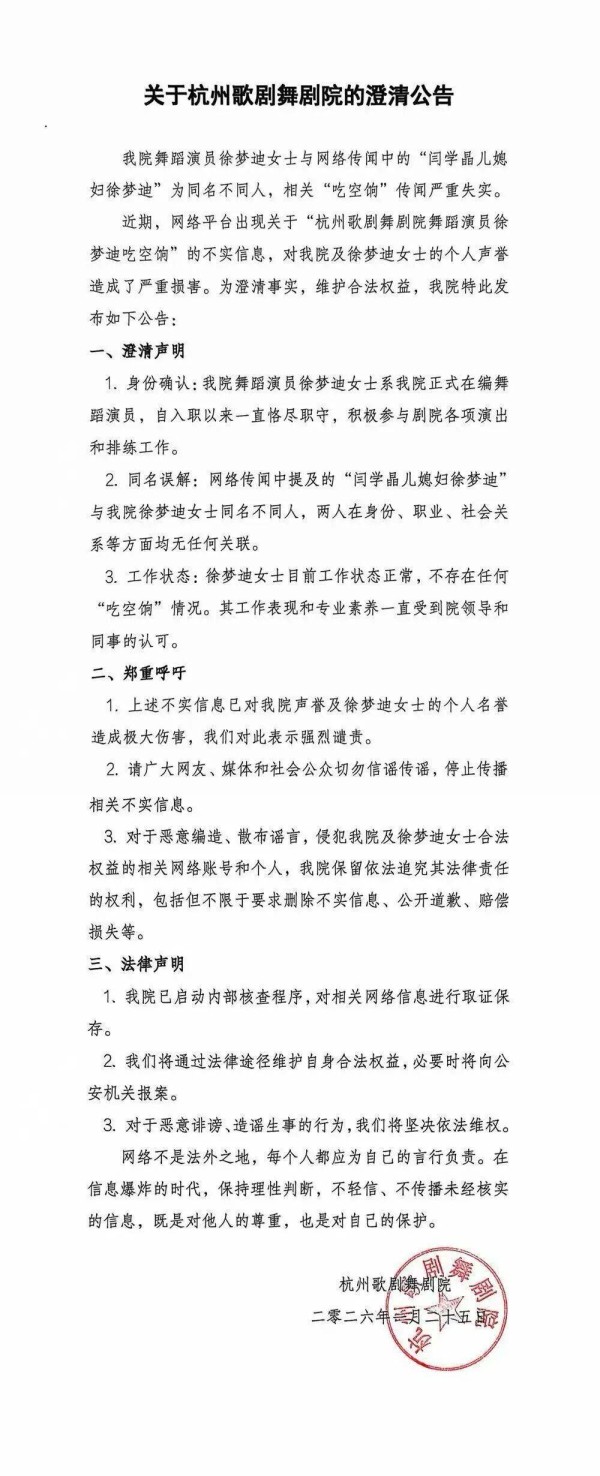记忆不灭,故乡永在
用故事记录生活,让记忆永不褪色。 #生活乐趣# #生活分享# #生活故事精选# #心灵鸡汤分享#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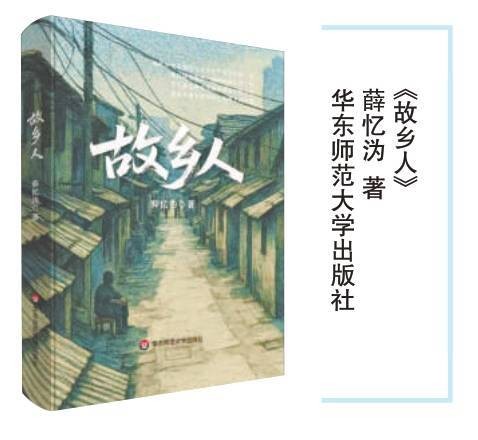
冯新平
薛忆沩的“故乡人”系列小说犹如一座记忆的迷宫,其中每一个个体都携带着故乡的碎片,在现代化快速推进的历史进程中踽踽独行。当《故乡》的主人公凝视长沙街头被古驰旗舰店取代的米粉店原址,当沃尔玛整洁的货架接替了曾经充满人情味的工厂家属区,这些物理坐标的变迁成为时代发展不可逆转的印记。薛忆沩的笔触在此刻化为一把敏锐的手术刀,他剖析的不仅是地理故乡的消逝,更是精神原乡在资本与速度冲击下的深刻转变——“故乡”由此呈现为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所言的“差异与重复”的迷宫,一个被重新编码的现代图景,个体的归属感在都市建筑的丛林中徘徊,化作难以安放的乡愁。
故乡消逝与记忆“量子态扰动”
然而,故乡的消逝并非无声的湮灭。薛忆沩将其转化为一场关乎记忆量子态的剧烈扰动。在《海燕》中,九旬老人通过儿子转述,惊异地得知自己曾是他人生命中的“引路者”——那位在“黎明前的黑暗”中鼓励绝望环卫女工仰望天空的神秘人。这段被他人珍藏的记忆,于她自身却是一片空白。这种“记忆的他者性”不仅暴露了自我认知的脆弱与流动——个体身份并非稳固内核,而是他人叙述与历史回响不断折射、重构的镜像;更揭示了记忆的量子叠加本质——它既是确凿的在场(对环卫女工),又是绝对的缺席(对老人自身)。唯有当“观测”发生——儿子传递文章《人生的十字路口》——这个叠加态才瞬间坍缩为确定的现实。这种悖论性在《初恋》中同样惊心动魄:“弹劾”一词从少年眼中恐怖的酷刑概念,在1979年4月那个决定性夜晚,因一句“原来她是被‘弹劾’走的”的灵光乍现,竟坍缩为连接两颗孤独心灵的密码与友谊契约。词语由此挣脱政治术语的冰冷桎梏,在私人情感的引力场中获得了全新的生命轨迹。
在此过程中,现代化浪潮作为强大的“观测者”,深刻地介入并重塑着个体记忆的轨迹。在《“国脚”》中,1978年世界杯转播开启的彩色乌托邦,其光芒被1977年恢复高考的理性洪流所遮蔽。表舅绿茵场上倒挂金钩的浪漫诗篇,在知识精英崛起的轰鸣中沦为喑哑的“前现代”遗响。小说更以辛辣笔触描绘“蜈蚣”摇头晃脑背诵《曹刿论战》的场景——古文语法对足球术语的碾压,是知识经济对体能崇拜的全面替代之缩影。于是,表舅辉煌的足球生涯被时代转型的阴影笼罩,其“国脚”称号从天赋的勋章转变为命运的负累,绿茵场也从荣耀的舞台蜕变为个体困境的象征。
而在《故乡》中,薛忆沩则借助高铁这一现代社会的标志,将速度带来的改变推向极致。车厢内的声响取代了绿皮火车上的星空夜话,窗外风景化作流动的画面,跨越省界江河也不再令人心潮澎湃。高铁不仅拉近了地理距离,也加速了传统情感联结方式的淡化。出租车司机依靠导航穿梭于名称相同却面貌各异的街道,健身设施覆盖了曾经播放露天电影的场地,长沙方言在正式场合逐渐淡出——最终,故乡的精神内涵在追求效率的浪潮中逐渐转化,成为一种略显疏离的符号,个体也在普通话普及的背景下,仿佛成了不断流动的原子。
代际传递与“隧穿效应”
然而薛忆沩的深刻在于,他并未沉溺于挽歌。其笔下的代际传递,宛如量子世界中的“隧穿效应”——尽管存在看似不可逾越的壁垒(代沟、时差、遗忘),精神的微粒子仍能奇迹般穿越障碍,实现联结与延续。《海燕》中的代际和解尤为动人:儿子试图以现代科技(跨国电话、网络文章)弥合鸿沟,却因语言和观念的错位一度加深隔膜。然而,当九旬老人在合唱队舞台上以颤抖却坚定的声音朗诵“在乌云和大海之间,海燕像黑色的闪电,在高傲地飞翔”,高尔基的文字瞬间成为穿越代际的能量隧道。衰老躯壳与年轻灵魂于此合二为一,文学之力消解了时间的线性暴政。她这只“老燕”的从容姿态与激昂吟诵,无疑成为台下师范大学新生——即将起飞的“雏燕”——最深刻的精神赋能。
代际传递的复杂性同样体现于《“国脚”》中。表舅生理上打破家族“短命诅咒”的突围,与其精神上困守理想牢笼的撕裂(退役二十年后仍珍藏“国脚”旧队服,却严禁儿子接触足球),形成触目惊心的悖论。更关键的是,这“以爱为名的暴力”与其父当年的阻挠如出一辙,构成代际创伤的闭环。然而颇具反讽的是,儿子对足球的漠然,意外消解了家族诅咒的暴力循环,无意中达成了另类的和解。由此,薛忆沩消解了简单的代际对立叙事,揭示出理想主义薪火相传的复杂性与坚韧性。
文学记忆的量子永动
那么,面对记忆坐标的消逝与现代化困局,救赎何以可能?薛忆沩将答案锚定于文学记忆的量子永动之中。当物理故乡在推土机的轰鸣中蒸发消散,精神故乡却以更强烈的文学形态辐射出来。《海燕》中构建的“虚拟原乡”最具启示性:通过“故乡情”网站、跨国电话、网络文章的偶然共振,20世纪70年代雨花亭的十字路口、波士顿的深夜、伦敦的海滩、合唱队的舞台在数字空间奇妙交织。于是,故乡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,而是由记忆碎片、文学意象与情感纽带编织的精神栖息地。
同样闪烁着精神微光的,是《故乡》中那座幸存的老工厂篮球场,是“傻杜”那句带着颤音的“他真是一个大好人”,甚至是那两个表面光鲜、内里悄然霉变的柚子中尚未完全腐坏的果肉。它们如同霍金辐射一般,微弱却顽强地证明着故乡精神内核的存在。而在《初恋》的结尾,叙述者在北上的列车中翻开李泽厚《美的历程》的一幕,则充满象征意味:当1979年的中国站在历史的门槛上,前现代的诗意与现代化的阵痛激烈碰撞。个体唯有在文学与哲学的星光照耀下,才能于记忆的废墟中辨认方向,重构精神坐标。
可以说,薛忆沩的“故乡人”系列,是一部以量子态书写的记忆史诗。在长沙街头迷失于“同名异构”的街道,在圆明园废墟聆听历史与私语的回响,在高铁车窗反射的面孔中寻找消逝的坐标——薛忆沩笔下的人物,在记忆坍缩与重构的永恒律动中,进行着悲壮的精神突围。当故乡的物理形态在资本与速度的洪流中分崩离析,薛忆沩告诉我们,救赎之光或许正蕴藏于柚子未完全腐坏的果肉中,在跨国电话中方言的微弱颤音里,在九旬老人朗诵《海燕》时“高傲飞翔”的姿态中。
因此,故乡从未真正死去。它只是从可见的地图坐标,转化为不可见的量子态,弥散在微信家族群转发的养生帖里,在尘封旧信中未寄出的炽热字句间,在DNA螺旋沉默的基因编码内。这些精神辐射的微光,正是我们对抗遗忘洪流的最后壁垒,也是重构灵魂原乡的永恒星图——在记忆的量子纠缠中,每一个灵魂都在寻找归途。(作者为书评人)
网址:记忆不灭,故乡永在 https://www.ashwd.com/news/view/189237
相关内容
真的是看一次燃一次,日月山河永在,大明江山永在……永生永世,不朽不伤不老不灭
11年不嫁不娶,真爱不灭
推荐《庆余年》给全世界,不灭亦不休
黑暗里,你是我不灭的光芒
Q:第二局鳄鱼带不灭的原因是什么?
“乘黄早已殉情,因爱执念不灭”
永在的清明,永存的价值
萧郎令裴郎嫉妒,丹青永存心意不灭
沉香不灭,悠悠缘长!我们永远支持淇淇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