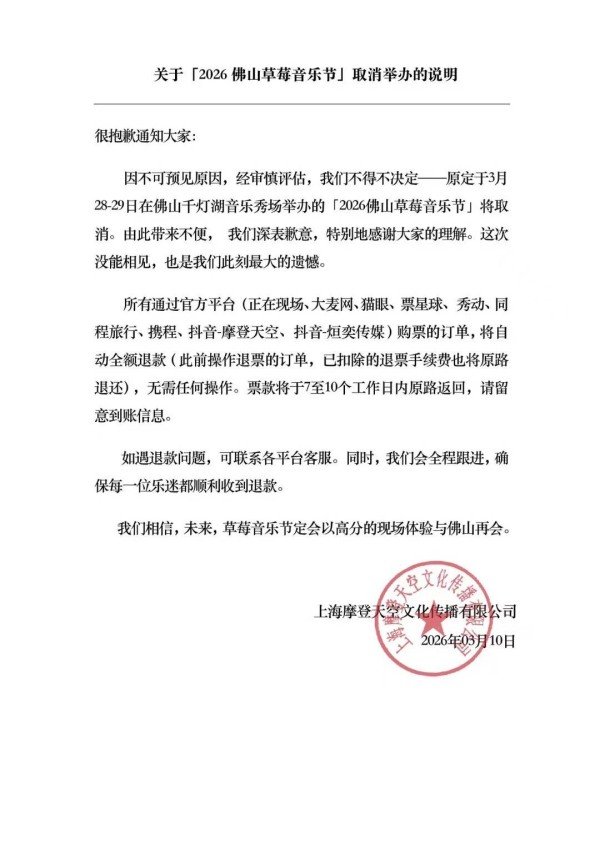再读威廉·戈尔丁的《蝇王》:文学镜像中极权社会的生成图谱
《1984》:乔治·奥威尔对极权社会的预言 #生活乐趣# #阅读乐趣# #经典好书推荐#
威廉·戈尔丁
威廉·戈尔丁是20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,代表作《蝇王》《金字塔》。他于198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仅有的四位英国作家之一。
《蝇王》《蝇王》发表于1954年,是威廉·戈尔丁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。《蝇王》不仅是一个关于儿童堕落的寓言,更是一部极权社会生成的微型编年史。文明的秩序脆弱如纸,一旦脱离外在约束,人性深处的黑暗便会催生出新的专制暴政。荒岛上的孩子们从表决、海螺号令的法治尝试,最终滑向杰克式的图腾崇拜、暴力统治,这一过程宛如一部加速播放的人类政治史,将极权从萌芽到确立的隐秘逻辑赤裸呈现。

然而,《蝇王》绝非孤例。当我们将其置于一条由众多文学经典串联的批判谱系中观察,便会发现,戈尔丁描绘的“荒岛极权模型”,实际上是不同时代、不同文明背景下,权力异化与人性质变这一永恒主题的又一震撼变奏。从卡夫卡笔下无形的压迫迷宫,到狄更斯描绘的维多利亚盛世暗面;从蒲松龄揭露的皇权吃人本质,到索尔仁尼琴记录的古拉格地狱——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一部关于极权社会如何形成、运作并吞噬个体的宏大叙事。它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理:极权并非现代社会独有的怪物,而是潜藏于人类制度与人心中,一旦条件成熟便会显形的幽灵。
文学镜像中极权社会的生成图谱在极权大厦奠基之前,首先是原子化个体的诞生。卡夫卡的《一则小寓言》为此提供了最精炼的隐喻:那只在逐渐收窄的大厅中盲目奔跑,最终落入猫口的老鼠,象征着现代人在庞大、匿名且异化的系统面前的绝对无力。无论是《审判》中K所面对的无名指控与荒谬法庭,还是《城堡》中土地测量员永远无法抵达的权力中心,卡夫卡揭示了一个关键前提:当个体感到无法理解、无法抗拒也无法逃离其所处的权力结构时,他便成为了系统潜在的合格零件——或牺牲品。

这种个体的无力感在狄更斯的《雾都孤儿》中获得了社会学的血肉。奥利弗·退斯特的命运从不因其个人品质而改变,只取决于他偶然落入济贫院、贼窝还是绅士宅邸。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浪潮中,传统社区纽带断裂,个人如同浮萍,其价值仅由其在经济链条上的位置决定。当社会将人异化为纯粹的生产或消费单位时,为更极端的、将人视为国家或意识形态工具的极权逻辑,铺平了观念上的道路。
极权并非凭空降临,它往往嫁接于深厚的专制传统之上。中国古典文学为此提供了悠久而深刻的见证。杜甫的《石壕吏》中,“吏呼一何怒!妇啼一何苦!”的对比,展现了皇权末端执行者绝对的、不容分说的暴力。老妇一家男丁殆尽仍被索求,最终只能“急应河阳役”,个体在战争机器前的渺小与无奈,揭示了专制权力无限汲取的本质——国家(或皇权)的需要永远高于个体的生存与尊严。
柳宗元的《捕蛇者说》则更进一步,提出了“赋敛之毒有甚是蛇”的著名控诉。蒋氏三代宁愿冒死捕蛇以抵赋税,因为系统的、常态化的盘剥比自然的、间歇性的危险更为恐怖和绝望。这种制度性暴力不仅剥夺财产,更扭曲人性,使人为了在系统中苟活而接受荒诞的生存逻辑。

到了契诃夫笔下,这种专制传统及其人性产物得到了更为细腻的剖析。《萨哈林旅行记》以报告文学的冷酷,记载了流放苦役岛上制度化的残忍与麻木;而在《胖子与瘦子》中,一次火车站的老友重逢,因官阶差异而瞬间演变成卑躬屈膝的滑稽剧。瘦子得知胖子官阶更高时,身体“蜷缩起来,弓着背,顿时矮了半截”,称谓也从“你”变为“您”。这一瞬间的变形,完美展示了等级制度如何内化为个体的条件反射,如何将平等的“人”异化为尊卑的“官”与“民”。恐惧与媚上,成为了专制社会流通的精神货币。
当传统专制与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结合,便产生了极权社会最富能量的燃料。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描绘了金钱如何撕碎最后的温情面纱。高老头的女儿们榨干父亲后任其孤死,拉斯蒂涅在目睹这一切后向巴黎发出挑战,完成了向野心家的蜕变。在这里,金钱不仅是财富,更是新的权力形态,它重塑了社会关系和价值标准,为一切道德沦丧提供了冰冷的合理性。
狄更斯在《艰难时世》中,刻画了功利主义哲学如何成为这种新秩序的意识形态内核。葛擂硬的“事实哲学”将一切简化为利益计算,最终导致女儿婚姻不幸、儿子堕落盗窃。同时,在《远大前程》中,皮普的“远大前程”完全建立在一个罪犯的秘密资助之上,一旦真相暴露,虚幻的上流社会身份便轰然倒塌。这两部作品共同揭示了,一个以金钱和实用成功为唯一标准的社会,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与精神的荒漠化。

马克·吐温的《百万英镑》则将这种金钱魔力以喜剧寓言的方式推向极致。一张无法兑现的百万英镑支票,仅凭其符号象征,就能让主人公亨利·亚当斯从遭人白眼的穷光蛋,瞬间变成众星捧月的上流贵宾。餐馆、服装店、旅馆乃至整个伦敦社交界的态度逆转,赤裸裸地展现了资本崇拜如何支配一切人际关系和社会判断。当货币符号成为衡量人的唯一尺度时,人的内在价值与尊严便宣告死亡,这为更全面的异化——将人异化为意识形态或国家权力的工具——扫清了最后的思想障碍。
当专制传统、资本异化与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,极权社会的完整形态便浮出水面,其最显著的特征是系统暴力的常态化与全民化。
茅盾的《子夜》展现了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在帝国主义挤压、官僚资本算计和内部动乱下的必然破产。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,更象征着在一个缺乏法治保障、权力可以任意干预和掠夺的社会中,任何基于理性和勤奋的经济活动都无法存活。国家权力与垄断资本勾结,吞噬了健康的社会经济细胞。

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罪与罚》中,则深入探讨了这种社会不公在个体心理层面引发的核爆。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——“不平凡的人”有权为崇高目的跨越常规道德——是其对社会“弱肉强食”逻辑的内化与极端化。他的杀人不仅是个人犯罪,更是一个被赤贫与不公逼至绝境的天才,对扭曲社会的一次畸形反抗。社会系统性制造了它的“罪犯”。
而索尔仁尼琴的《古拉格群岛》,则是对极权暴力最终形态的终极记录。它超越了文学,成为用无数受难者姓名和血泪铸就的史诗级证词。书中揭露的不仅仅是酷刑、荒谬的司法和超强度的死亡劳改,更是整个社会如何在恐惧中变形:夫妻相互告密,朋友瞬间背叛,沉默成为普遍的生存策略。古拉格不仅是地理上的群岛,更是心理上的群岛——它将恐惧与怀疑植入每个人的心中,彻底瓦解了社会信任与道德基础。在这里,人不仅被奴役,更被系统地改造为奴役的参与者或冷漠的旁观者。
回到戈尔丁的《蝇王》,我们便能理解这部小说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概括力。荒岛,正是一个剥离了所有历史包袱和社会复杂性的纯净实验室。

初始状态(法治的尝试):孩子们模仿成人社会,选举拉尔夫为首领,以海螺为议事的象征,试图建立规则与秩序。这对应于人类对理性、法治与社会契约的最初向往。
第一道裂缝(恐惧的滋生):对未知“野兽”的恐惧,成为理性秩序的第一道裂痕。恐惧是专制最古老的盟友。杰克敏锐地利用并放大了这种非理性恐惧,将狩猎和献祭塑造为对抗恐惧、提供安全感(肉食)的强力方案。
权力转移(生存压倒理想):当拉尔夫领导的议会无法有效解决生存(获取食物)和安全(驱除恐惧)这两个最根本的问题时,他的权威便开始流失。杰克的猎手队伍,因其直接满足生存需求并提供集体宣泄(狩猎仪式),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。这揭示了极权一个关键的吸引力:它在危机时刻,往往比繁琐、低效的民主程序显得更“有效”、更“有力”。

暴力夺权与恐怖统治:杰克不再满足于权力分享,他夺取了象征智慧与文明火种的眼镜,通过暴力清除异议者,并最终对拉尔夫展开猎杀。海螺——法治的象征——被砸碎,篝火——求救的理性希望——被滥用于暴力目的。一个以杰克为主导,以暴力为法则,以对“野兽”的恐惧为凝聚力的微型极权社会宣告完成。
拯救与反思:军舰的到来,外部成人世界的干预,中止了荒岛的悲剧。但救他们的军舰本身正处在战争之中,军官身上仍带着暴力的印记。这暗示着,所谓的“文明世界”并非暴力的绝缘体,它可能只是将暴力包装得更为精致而已。拉尔夫最后的哭泣,是为“童贞的丧失”,为人性之恶的显现,也为这短暂而残酷的极权实验。
《蝇王》的伟大在于,它寓言般地演示了极权如何从人性普遍的弱点(恐惧、自私、从众、对强力的崇拜)中滋生,如何在“现实需要”和“更高目标”(生存、安全)的包装下获得合法性,又如何通过一步步蚕食规则、垄断暴力、制造敌人来巩固自身。它与我们回顾的整个文学谱系遥相呼应:极权社会的形成,很少是一夜之间的政变,而更多是一种“慢动作的坠落”,是理性被恐惧侵蚀、法治被效用怀疑、个体良知被集体狂热吞没的渐进过程。
网址:再读威廉·戈尔丁的《蝇王》:文学镜像中极权社会的生成图谱 https://www.ashwd.com/news/view/207202
相关内容
广东作家王威廉科幻作品荣获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《威廉·莫里斯传》:一位理想主义者的燃烧人生
再读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:金钱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
阿道司·赫胥黎:预言未来社会的反乌托邦小说家
谢锦×走走×金理×林戈声:当“纯文学”遇上“发疯文学”
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·略萨逝世 享年89岁
“独眼狮王”沙拉普特丁·马戈梅多夫(Sharaputdin Magomedov)称重:185磅
邱丽苏@胡杏儿 让丁达尔向作弊的同学赔礼道歉,丁达尔@徐崴罗 坚决不干
再读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:专制社会就是一个“吃人”的社会
戴锦华谈电影:重访戈达尔、塔可夫斯基、安哲罗普洛斯